警惕美国军工复合体新演变

3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白宫签署行政令前讲话
文/李峥
编辑/黄红华
在华盛顿的权力长廊与全球地缘政治的复杂棋局中,美国军工复合体如同一头庞大而沉默的巨兽。在特朗普开启第二个任期后,这一巨兽再次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特朗普誓言削减军费中的“浪费”,又希望推动美国武器出口和全球军事合作。美国军工复合体正在成为一个跨国、跨行业的权力网络,渗透到政治决策、经济利益和国际关系的核心。当盈利驱动的私营企业掌控军事命脉,当武器出口点燃新的军备竞赛,全球和平的脆弱平衡还能否维持,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硅谷化”新趋势
1961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军工复合体”这一术语,警告其可能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他指出,冷战时期军事需求的激增催生了一个由政府、军队和私营企业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巨额合同和政治游说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利益循环。
军工复合体的核心在于其“铁三角”结构。美国国会通过增加国防开支为选区带来就业机会,国防部依赖私营承包商提供武器系统,而企业则以政治捐款和游说回报支持。据统计,美国主要军工企业过去8年来向国会议员的政治捐款超过8700万美元。这种关系不仅扭曲了预算分配,还导致军事开支优先于教育、医疗等社会需求。
军工复合体不仅是经济实体,更是“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层国家指政府内部通过非正式渠道影响政策的权力结构,而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旋转门机制和情报共享深度嵌入其中。例如,特朗普第一届任期内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曾是雷神公司的资深游说员。这种交织赋予了军工复合体巨大的政策影响力。在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五大军工巨头的游说下,F-35战斗机项目虽因成本超支和性能问题饱受诟病,但仍然能获得持续拨款。
近年来,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发生了深刻变革,传统的航空巨头正逐渐让位给硅谷的科技新贵。人工智能、云计算和无人机技术成为现代战争的新前沿,也成为军工复合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帕兰提尔公司(Palantir)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成为五角大楼的情报支柱,其市值达到2200亿美元,达到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市值的总和。Anduril则凭借自主无人机和AI技术,赢得了协作作战飞机的原型合同,标志着科技公司正式跻身军工核心圈。
这种“硅谷化”趋势源于五角大楼的主动转型。2015年,国防部成立国防创新单元(DIU),为初创公司提供资金支持。2016年至2022年,DIU向320多家初创公司提供了12亿美元的合同,微软、亚马逊等巨头也在2018年至2022年间承接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国防合同。这种合作不仅重塑了战争形态,也让美国军工复合体与科技巨头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美国前总统拜登在其告别演讲中,首次公开警告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形成的“科工复合体”,表达了对于科技企业介入军工产业的担忧。
特朗普打破传统“铁三角”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迅速将矛头对准军工复合体的高成本。他在竞选期间公开抨击F-35战斗机项目,称其“完全失控”,并迫使洛克希德·马丁下调了合同价格。2018年,他又要求五角大楼重新谈判波音的“空军一号”改装合同,节省了约14亿美元。这种强硬姿态让外界一度以为,特朗普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之后首位真正挑战军工复合体的总统。在特朗普持续施压下,美国军工复合体确实有所收敛。然而,他的行动更多停留在表面,在其第一任期,美国国防预算仍稳步攀升,军工企业的利润并未受到实质性冲击。
进入第二任期后,特朗普的政策延续了这种矛盾。一方面,他继续高调批评军费“浪费”,要求五角大楼压缩不必要的项目开支。上任后,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对所有重大国防采购项目进行审查,任何成本超支或进度落后的项目都可能被取消。与此同时,特朗普又提出将国防预算提升到1万亿美元规模,试图“重建”美国国防工业。
特朗普对科技的偏爱则为军工复合体注入了新的变量。他青睐Palantir和Anduril这样的公司,认为它们的AI与数据技术是“未来战争”的关键。此前,Palantir及其主要投资人彼得·蒂尔与美国右翼关系密切,为特朗普竞选投入大量资金支持。这种特殊地位让少数科技企业可能在军工复合体中拥有特殊地位。另外一个可能对美国军工复合体带来更大影响的是特朗普的主要金主马斯克。马斯克及其企业虽然不直接介入军工产业,但其“星链”和商业航天火箭却具有巨大的军事功能。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DOGE)也试图将美国军事部门作为重要审计对象,这可能将打翻诸多美国军事承包商的饭碗。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内阁构成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一关系。特朗普的副总统万斯、防长赫格塞思、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都曾有丰富军旅经验,但也对美国传统军工企业一直持批评立场。赫格塞思曾作为国防承包商与军方合作多年,并利用军方合同赚到“第一桶金”。新任副防长范伯格是一名拥有50亿美元身家的富豪,曾拥有一家私人军事安保公司。这些人掌握着设计美国国防预算的大权,也间接影响着诸多美国军工企业的命运。国会在军工复合体中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行政部门的地位则显著提升,这种变化正在打破军工复合体传统的“铁三角”结构。
美国军工复合体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特朗普“退群毁约”的孤立主义政策。他对北约的质疑和与盟友的紧张关系,削弱了美国在欧洲的武器市场。2025年3月,欧盟宣布投入1500亿欧元打造自主国防工业,明确将美国公司排除在主要合同之外。这一决定不仅威胁到美国军工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促使欧洲国家加速军事现代化,间接加剧了全球军备竞赛。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让美国军工企业面临新的压力。关税及其在全球引发的反弹让美国军火商的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美国媒体认为,中国的反制措施让美国面临稀土、关键金属、原材料的供应紧张,而这又将直接传导到美国军工产品的成本之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导致F-35等项目的供应链成本上升,引发了洛克希德·马丁等企业的不满,这些企业的股价近期出现显著下跌。
私有化推升“失控风险”
科技巨头的介入和特朗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冲击让美国军工复合体面临新的生存环境。传统的“铁三角”模式正在被逐步打破,美国军工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更难以“躺平”。在这种压力下,美国军工企业向外扩张的冲动被迫显著加强。
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美国军工企业的武器出口占全球的近40%,客户遍布日本、印度、沙特等地。新兴市场如越南和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游说下加大了采购力度。这种全球化不仅为军工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也在无意中点燃了新的军备竞赛火种。
全球化不仅为军工复合体开辟了新市场,也为其在国际危机中的角色埋下了伏笔——从乌克兰战场到中东冲突,它既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又是问题的放大器。乌克兰危机期间,印度与俄罗斯的武器交易因美国制裁受阻,促使其转向美国供应商,但这并未缓解南亚的紧张局势。相反,巴基斯坦随即也加大了军事采购,导致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军工复合体的市场扩张,正在将全球安全推向一个更加不稳定的边缘。
在国际化的同时,私有化成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另一大趋势。更多隶属于个人或少数投资者的科技企业、新兴军工企业不仅在美国国内逐步做大,也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业务,成为拓展国际市场的先锋。在乌克兰危机中,私营公司如Palantir和SpaceX提供了关键的情报和通信支持,也从中赚取了巨额利润。近期,Palantir拿到了北约总部的人工智能大单,成功将触角伸入欧洲防务市场的腹地。与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传统军工企业不同,Palantir和SpaceX的投资者更为集中,创始人在企业中的话语权巨大,几乎难以受到外界影响和监督。
私有化的新型军工企业可能让美国军工复合体成为一股“失控的力量”。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黑水”等私营安全公司承担了大量任务,却因滥用武力和缺乏监管引发争议。如今,这种模式带来的问题可能会扩大到全球层面。新的美国军工复合体将处于美国国内和外国法律的中间地带,由于其特殊业务受到较少监管,更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意志之外的“影子力量”。这一头可能失控的巨兽的规模和复杂性已远超艾森豪威尔的想象,可能将冲突推向更长的轨道,甚至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动荡。
特朗普与军工复合体的博弈,折射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政策既试图约束这一“巨兽”,又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松绑;既承诺效率与和平,又无意中助长了全球紧张局势。如果不加强监管,推动国际军控合作,那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民众都可能成为这头巨兽新的捕食目标。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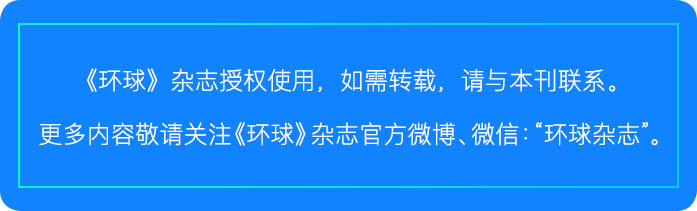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